

从经济学视角看,任何行为方式的相对固化、交易的达成,都经过反复博弈。通过反复博弈,交易双方形成相对固定的达成交易的方式与认知。香港历次动乱中亦如此。

文/《汽车人》评论员 赵英
前段时间,除关注中美贸易战,就是关注我的老本行——汽车工业。对偏处南方一隅的香港,偶尔看看电视,知道那边有几个黑衣人在大街上胡作非为,对政府机构、商店、公共设施进行打砸抢,对普通百姓为所欲为。尽管如此,由于的确对内地影响不大,就想随它去吧!前几次不也是折腾个够,然后趋于平静嘛。

但是,延宕至今已三个月了,暴徒们依然在上演扔燃烧瓶的戏码,甚至开始抢枪。这种丑陋的“激情表演”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激情”发展到疯狂,会产生何种后果?即便“激情表演”暂时平息,今后会不会随时上演?这些都是关系香港长期稳定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影响中国发展与安定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似乎有必要写篇文章。

近日在网上读到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接受采访的讲话,他说:“我最害怕见到的就是一般老百姓开始无视法律,现在有一些上班族,早上坐地铁也跳闸了,跳栏了;开车可以违规,大家已经觉得好像他可以扔汽油弹,我冲个红灯算什么?这个是很害怕的一点。大家累积下来那么多年,对法律、法庭、法官的这种尊重,这种听从,一下子被搞没了,我觉得这个对未来香港的影响很大。从一个普通的市民来讲,怎么好像犯法的成本那么低,这个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这段话,深合我意,也使我这个只是路过香港机场,被机场服务人员翻过几次白眼的人,觉得可以写上两笔。
另外一件事,也促使笔者不得不写上两笔。香港头条日报网报道,准律师朱承晔在网上发表“黑警死全家”等仇警言论,遭人投诉行为不当。他辩称有关言论并非他的意见,而是女友用其账户发表,他知道后立即删除言论,并永久删除了该脸书账户。
9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接纳了他的解释并批准他宣誓成为律师。法官陆启康同时提醒说:“香港司法制度行之有效,要靠法官、检控、律师和警察等不同方面履行职责,他们应互相尊重,理性解决分歧;本次朱的有关言论绝不理性,更针对警察及无辜家人,极不恰当,提醒他吸取教训,日后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律师。”香港真是神奇的地方!如此仇警,散布恐怖言论的人,把责任往女友身上一推,即成为律师。太不可思议!
正因为如此,促使笔者写作此文,探讨这些神奇的人和事,为什么出现,并且屡见不鲜。
对香港乱局的前因后果,已经见到若干深有真知灼见的文章,笔者想从经济学视角对香港乱局,做一点略有新意的解释。

香港回归前,中央政府确定了“一国两制”收回香港的大政方针,确定了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体制,同时也确定了香港回归后的治理体制。
“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都是一个创造。通过“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使我国政治体制有了更大包容性,对促进改革开放、国家统一、香港平稳过渡,都是必要的。
“一国两制”意味着主权完整,在一国之下,治理和运营体制相对区隔。注意,笔者这里讲的是“相对区隔”。据笔者所见,迄今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对“一国两制”是制度、治权的相对区隔,关注不多。香港回归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在落实“一国两制”时,也是强调“不同制度”比较多,对相对性带来的影响,缺乏深入考虑。
实际上“一国两制”本身就意味着“两制”是相对的,“两治”也是相对的。首先,香港特区基本法的制定,意味着香港政府施政要在法律范围内,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其次,中央政府保留了香港驻军、外交权、维安权;第三,特首的选举和任命(包括主要官员),需经过中央政府;最后,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难以离开内地,尤其是大湾区。
上述因素的存在,意味着在“一国”之下的“两制”,不可能绝对区隔;意味着中央保留的某些权力必然穿透“两制”,参与香港治理。香港回归以来,遇到几次重大危机(索罗斯袭击金融市场;萨斯危机)不正是中央政府出手相救吗?这也正是香港某些势力感觉很不舒服,动辄闹事的原因所在。
如果真是“两制”完全绝对区隔,就会产生英国当局在交回谈判香港谈判中提出的所谓“主权换治权”。这一点我们务必要有清醒认识。下面还将分析,域外势力及香港本地某些势力所争、所闹者,也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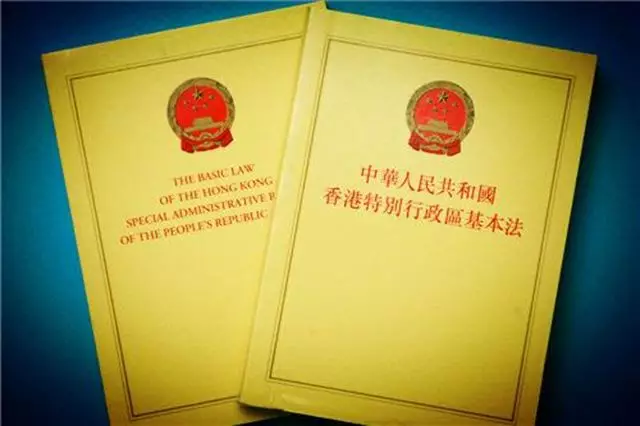
正是由于“两制”的相对性,导致“两制”之下如何治理,如何划分治理权力,存在灰色地带。香港回归前,各利益相关方围绕《基本法》制定的磋商,实际上就是在具体治权上如何分割的博弈。
这个灰色地带,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予以确定(现在看司法权失手是一大失误)。但如何运作,在50年不变情况下某些利益集团如何利用形势,利用法律漏洞为自己服务,却难以逆料。例如,第23条虽然写在基本法上,却至今未能落地。
在“一国两制”政治体制中,主权属于中央,治权的大部属于特区政府。这种治理模式,类似于经济领域的“委托-代理模式”。经济领域的“委托-代理模式”,意味着财产权和经营权相对分离,财产所有者(股东)通过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经理班子负责企业运营。
这种经营模式下,经理班子有很大权力,但董事会可以通过考核业绩、人事任命、重要事宜批准、股权激励等手段,制约经理班子,甚至撤换。在这种经营模式下,存在着经理班子甚至总经理个人,为一己之私,做出不利股东利益决策的可能,存在着发生代理风险和提高交易成本的问题。

“一国两制”体制中,中央与特区政府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不过是“政治领域”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董事长)对香港特区政府(经理班子)授予大部分经营权,只保留了维护安全、驻军、外交的权力。仅有的这些权力,在行使上,还受到很大局限:基本法23条迟迟未能落地;香港政府也有某些开展国际活动的空间;驻军只能在特区政府请求时,才能出动。
这种权力分割,使主权拥有者在法律框架内有限的权力运用受到规制情况下,主动行动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一旦有事,主要看特区行政班子如何作为了。至于平时运作则完全委托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的构成,除基本公务员队伍外,政务领导及高层行政官员是依据基本法挑选出来的行政、技术、法律精英,这些人具备足够技术层面的知识和能力,但不是政治家。
毋庸讳言,中高层公务员中,某些人与海外某些势力,与香港大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身在曹营心在汉”。陈方安生就是其中的典型败类。在香港公务员队伍的中下层,还有相当一批拥护原港英当局的人。从这次动乱公务员队伍中内鬼频出、乱象不断,就可以得到证明。

特区政府在治港理念上,不折不扣地继承了原港英当局的“积极不干预”理念,也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念。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原特首曾荫权在香港政府入市干预股市,击败索罗斯后,反而痛心疾首地放声大哭的情景。
原港英当局,在试图“以主权换治权”失败后,进行了一系列运作:修改法律、扩大议会权力、推动所谓“民主”;削弱政府行政权力和权威;授予相当一部分人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隐蔽某些谋略机构;培植英国代理人;在文化界和教育界巩固和占领反华阵地等等。通过这一系列布置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为后来屡次挑战中央政府埋下了伏笔。
香港回归后,香港的大部分治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运作的。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不折不扣地落实了“一国两制”,并在香港需要时出手相助。但特区政府“积极不干预”的治理方式及资本主义体制,导致隐患丛生。这次动乱就显示了各方面长期不作为、治理失败的恶果。

香港底层百姓,尤其是青年人看不到未来,具体地说就是对走出“笼屋”失去信心,是这次动乱的重要原因。香港不缺土地,建筑“经济适用房”却难于上青天。董特首、梁特首的规划,形同废纸。房地产财团在香港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最奇葩的是,香港的公用事业,居然基本控制在“李嘉诚”们手中,等于财团垄断、掌控着旱涝保收的印钞机,随时榨取香港百姓。
香港迄今为止运行的是近乎原始的资本主义。在欧洲,甚至美国,对公共事业运营、普通百姓基本福利,都在原始资本主义基础上做了较大修正。政府要做出努力,让百姓享受的福利从公平、正义角度起码过得去。财团如果有垄断行为,则有反垄断法伺候。这两天谷歌等网络巨头正面临着美国国会的审视。
香港的财团运作,则似乎完全用不着担心反垄断。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认真履行。贫富差距拉大,正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从香港几大财团集聚之烈、百姓寻找立锥之地之难,可以看出经济治理之失败。

此次动乱,没有好好上学、错别字连篇的“废青”冲上街头;大学成为“港独”势力集聚之渊薮,港独学生冲击校长室,胁迫其他同学,为所欲为;通识课本上充斥港独谬论。可见教育治理之失败。
此次动乱,《苹果日报》等无耻报刊,煽动暴乱于前,支持暴徒于后,公然挑动港独,然而至今安然无恙。众多不良媒体,专门有倾向性地报道警察活动,完全无视暴徒为非作歹。某些所谓“记者”公然在记者会上问林郑特首“何时去死”。可见文化、新闻治理之失败。
此次动乱,暴徒横行街头、闹市、公共场所,一旦被警察执法抓捕,前脚进,后脚出,外籍法官立即放人。“汉奸”黄之锋两次被抓,竟然大摇大摆地逍遥法外,远赴欧美,摇尾乞怜,勾结欧美政客,制裁中国。这在全球范围,也是一大奇观。可见司法权根本不在中国人手中。司法权失控,等于法律有效性不复存在,警察执法,形同虚设。
此次动乱,某些外国机构、宗教组织,公然活动,指导颠覆特区政府。某些外国机构在港人员的编制,达到上千人。此为基本法23条迟迟难以落实之恶果。

从上面的分析看,今日香港之局面,既由内外恶势力勾结、策划、煽动,也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治理不力、治理能力弱、治理理念存在问题所致。
在上述治理背景下,我们再进一步分析香港某些势力的行为方式。从经济学视角看,任何行为方式的相对固化、交易的达成,都经过反复博弈。通过反复博弈,交易双方形成相对固定的达成交易的方式与认知。香港历次动乱中亦如此。
第23条立法,某些势力煽动民众上街,特区政府撤回立法动议;推行国民教育,某些势力煽动民众上街,特区政府撤回了;某些势力鼓吹“双普选”,实行“占中”,制造混乱的人毫发无损,维持秩序的警察被判入狱;此次动乱,特区政府撤回对“逃犯条例”的修改,动乱分子变本加厉,不仅借此公然鼓吹港独,甚至把暴乱升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从挑动动乱的高层分析,这些幕后势力操纵民众,屡屡得手,使他们测出了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的底线,所以一旦有对他们不利的行动,动辄煽动民众,已成惯用手段,并日益熟练。
回顾历次动乱,这些势力每次都把暴力向前推进,逐步演变成今天的态势。此次动乱实际上已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反修例)。看到中央政府的“底牌”后,他们可能想见好就收,所以才有“宽容年轻人犯错误”的惺惺作态。那些能够上台面的年轻头目,基本上也达成了个人目标,由“废青”,转变为西方著名学府的学生。底层“废青”走向如何呢?

底层“废青”同样有自己的总结。一来本身就没有工作,或正经工作薪水甚低,上街一天,所获颇丰;二来上街使用暴力,不担心警察反击,香港警察小心翼翼地证明自身是全世界最文明执法的队伍,也正因为如此,暴徒无需恐惧,即便进了警察局,还有一大帮热心法官施以援手;三来自己的行为仿佛可以使灰色人生有了亮点,自己在团伙中,在某些势力关照下,收获毒品、女色(香港媒体报道)。即便打爆眼睛,也会收获巨资。
总结以上分析,当参与暴乱成为有收益、没损失、成本甚低的活动,当暴徒成为一种职业,“废青”没有理由不上街折腾。如果继续有人给他们发工资,他们不会自愿“下岗”。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有样学样,暴徒还可能增加,只要幕后老板愿意继续开工资。
据中新社香港9月23日电,香港警方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过去周末暴徒的暴力全面升级,袭击警员及殴打市民常态化。自6月极端暴力违法事件发生以来,截至22日共有1556人被拘。注意,“袭击警员及殴打市民常态化”,这种状况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当暴徒成为职业。
长此以往,如果特区政府和香港民众真能忍耐,暴徒上街将成为日常“行为艺术”,但对香港旅游业并无促进。

香港动乱至今,已过了伟人说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阶段,多数人感觉上街是一场噩梦。但是,领工资的暴徒不这么想,幕后老板不这么想。他们不敢公然成立港独政府,但通过肆无忌惮地架空、无视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治权,实际达成港独,或许是他们的妄想。
笔者在这里正告这些跳梁小丑:港独的清秋大梦,趁早算了吧。(文/《汽车人》评论员 赵英,部分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所有。如需转载,转载方必须与“汽车人传媒”(邮箱:qcr007@126.com或电话:010-63135250)联系,获得同意取得转载授权,否则必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