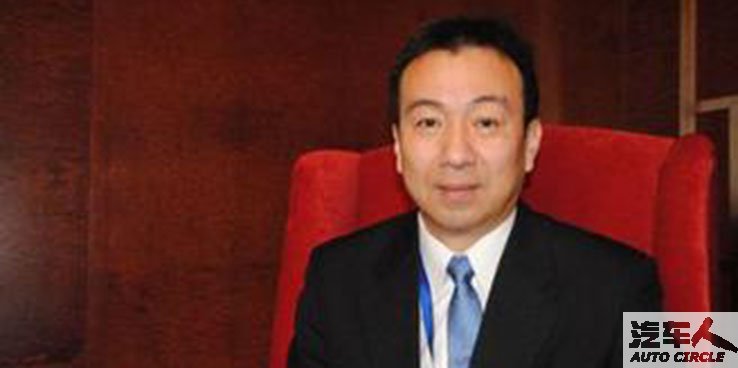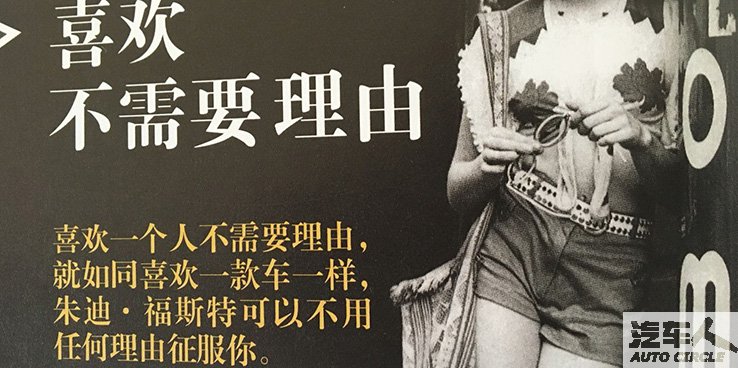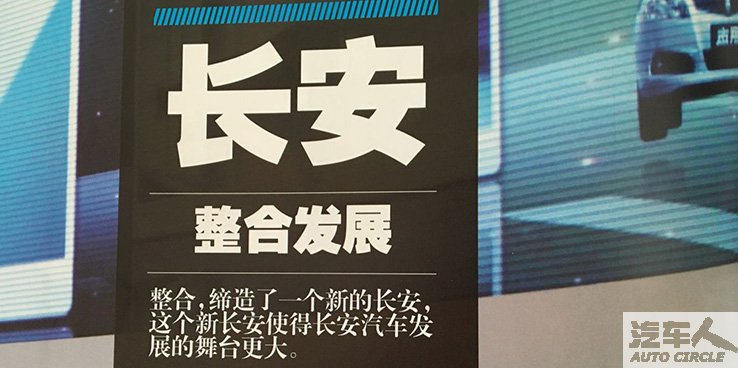邢如飞,伴随着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的独立门户,这个名字和这个人开始更多地见诸报端。早在几年前,他还是华晨汽车研发中心的总经理助理,那时,意气风发,只知造车,时而接受媒体的采访,也都是技术层面的,从容不迫,对答如流。
一如从前,衣着随意,但简洁精干,随处都透露着技术出身的特点。作为华晨最新一个重要门户的一把手,邢如飞给人的感觉却相当平和,像极了小学生作文里常用到的一个词:“平易近人”。
他说他没有什么大的理想,一切顺其自然就好。在记者采访的时候,他甚至会时不时地问身边的人:“这个我能说不?”显然,他并不热衷于做一个新闻发言人,而更倾向于做一个扎扎实实做技术的工程师。
但不管他是否愿意,此后,他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出镜”机会,越来越多的“答记者问”还将等着他……
他淡然,喜欢随遇而安,但对于技术方面又格外地专注。华晨汽车工程院院长这个技术与管理双重叠加的角色,他将如何实现风格的转换,抑或这就是他独有的“邢氏作风”?
新角色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这一点在邢如飞身上似乎并没有体现出来。
也许因为变来变去都还是做技术,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围绕“技术”二字所进行的实质性工作。
“研究院独立出来以后,工作内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主要是到集团之后,祁总比较重视,我们要求每个月都要汇报。”他笑起来,“总的来看,对研究院内部肯定是要求比以前高了,这就比以前压力大了,特别是新产品的输出质量,要求就更严格。当然,以前做也是按照要求做的,现在要更准时,输出质量要更好。”
而从产品规划角度来讲,思路也要放得更开了。作为领导者的邢如飞,也需要开始从总体上把握产品的研发方向。
“以前华晨金杯每年的开发任务,这是我最主要的(工作),对产品的后期规划,不用太操心,但现在必须得从集团的高度来考虑。”对于邢如飞来说,以前大多是考虑当年的产品规划,至于长远目标不会太涉及,因为上面还有监管会、董事会,然后才到研发这一级,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如今,他需要直接面对华晨董事长祁玉民,后期几年的产品规划都必须由他主导。显然,这不是一般的重任。从目前正在着手的项目来看,他已经在适应这种从长远布局统筹规划的作战方式,但还只能说是在逐步“适应”中。
作为年轻的领导者,邢如飞坦言自己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技术层面的动力总成。随着沈阳的开发业务都划分到研究院,相对于原来的研发中心,现在的研究院必须担负起整个发动机的开发业务。
“动力总成是车的核心,而且所有车型的开发实际上都是从新的动力总成开始的。”邢如飞并不讳言华晨这方面不强,并认为这块业务需要加强。尽管以前也在做这块业务,但做得比较散,没有规模性,现在集中规划,集中开发,对华晨集团来说,加强其势弱之处,这是一件好事。
2.85亿的遗憾
对于邢如飞来说,在华晨16年的技术生涯,已然不算太短的经历。问其值得铭刻在心的记忆,他并没有高谈阔论什么,反倒是M3的失败让他难以释怀。
2003年年底,邢如飞接手M3,即华晨轿跑“酷宝”,然而这却成为他一生的“心理负担”。因为M3正是他担任的项目经理,而这个车,用他的话来说,卖得不好。
实际上,这车的确卖得不好。但无论从外形上还是目标受众的定位,M3都是无可指摘的。遭遇市场这样的滑铁卢,显然是邢如飞以及当时参与研发的一干人的意料之外。
时隔多年,邢如飞已经能够平心静气地分析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失误就是当时市场定位没做好。”但事实上,项目初期是做过非常周密的市场调研,包括后期的量和价格预测都是很准,为什么实际的效果反差会如此之大?
他犹豫了一下,对《汽车人》说:“不怕你笑话,当时我们就想做一个什么呢?想做个中国的Mustang,野马。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年轻人开始挣钱了,得给他们做台车。”
雄心勃勃的一帮人,开始为自己的想法欢呼雀跃,摩拳擦掌,他们觉得中国可能进入Mustang时期了,那么现在就要抓住机会。直到做完之后忽然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还早着呢。”他无奈地笑。
提到当年的失败,邢如飞始终认为自己主观臆断的东西太多了,一直耿耿于怀。记忆中,“做好的地方没什么印象,做不好的地方,就M3,对我的打击特别大。2.85个亿呀,每一分钱都是我花出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挣回来。”笑容背后,是他看不见底的压力。
对于这一款“失败”了的爱车,邢如飞仍旧掩饰不住爱惜之情。“车做得应该还是不错的……车做得还不错。”他低低地重复。但是如果要冲量,这款车显然力有不逮。
而关于M3的未来,他又舍不得彻底放弃这一平台。所以他考虑想办法在研发部弄个地方,将M3转入小批量的生产方式,以个性化的方式去销售。这样的话,“生产就解脱了。这边投入占了这么大的生产场地,这么多固定人员,这不行,不合适。”
当然,对于接手研发之后的成果预期,他并不急切 “一个还没出来呢。不能这么快,呵呵。”这样的心态,反而让人对他更有了信心。
《东周列国》与“暗香”
出身于理工科的邢如飞,爱读《东周列国》等古籍,这一点倒颇为出人意料。但不时流露出的书卷气和对人对事淡定而为的行事风格,又让人不得不信服于此。
对于现在的位置,他甚至认为,其实让自己来担当这样一个责任,只是出于“总得有人挑头儿吧”,于是,他就接手了。而这样的想法源自于对华晨这个研发团队的挚爱,他坚持认为这里不一样,是超出了普通同事关系的战友之情。
“这个研发团队,十几年前就是很多人一起开始的,可能有些人都超过12年,都是我们很多年的同事,”长年以来的摸爬滚打,让同事之间甚至上下级之间都有了超乎寻常的深厚情谊。“这么说吧,我们之间的关系像集结号,像战友这种关系,有困难大家一起上,车做好了大家也挺高兴,有问题就下回再把它弄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下级之间没有很明显的界限,工作的时候,严肃中不乏小趣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开玩笑的时候也开玩笑,说正事的时候说正事。这种看似松散的管理方式,很大程度地冲淡了研发人员肩上的压力,却又不乏工作上的凝聚力。
他说他这种管理方式其实受一位业界的前辈影响很大。“我以前性格也不好。我之前有个师傅,叫秦仲年,原来是上汽的,后来在这边。这个人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介绍,师傅的最大的特征,是39年没跳过槽,一直在上汽,直到退休到这边干了3年。其人处事一直很低调,靠很亲和的方式去交流,听大家的意见,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把握得很准。
“他在整个圈子里名声非常好,后来业界有人评价过他,叫他‘暗香’。”说到这里,他一脸的崇敬之情。
正是受了这种“暗香”的影响,以及成长环境的潜移默化,使邢如飞有着淡定的人生观。但坐到这个位置上,就必须要有一些领导的权威性和震撼力,这样才能够在正事上果断坚决。“技术和管理的事他们非常怕我,这个你不用担心。”他笑着打消了记者的顾虑。
下一台车永远是梦想
“做车就是总想着做下一台车一定要做好,下一台车永远是梦想。”这是邢如飞的态度。
但现实和梦想总是有差距。尽管对于邢如飞们造车的人来说,能够引起他们最大兴趣的,是做变化很大的、很具有挑战性的车。但是,“说实话,做这种车对公司来讲风险也是很大的。公司必须要稳健发展。不能今天这明天那的。要稳,必须得稳。要盈利,这是很关键的。”
而企业如何盈利,已经渗透到研发之初的产品定位等一系列规划之中。就此而言,盈利也成为技术出身的邢如飞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自主品牌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必须得找到一个合理的盈利模式。做出来一个车,需要能够保证一个很好的利润。”但风云诡谲的中国市场,变化太快了,包括供应商体系、制造能力、市场等等诸多参数里面,变量太多。就自主品牌来讲,在这样一个市场里保证一个产品做出来就是盈利的,难度越来越大。“对我们来讲,这就是最大的挑战。不是说把这个车做得跟通用做到一个水平上,这个难,最难的是做到一个水平上,又要比它便宜好几万块钱,然后还得卖出去,我还得挣钱。这是很困难的。”
邢如飞也在为这样的问题头疼。但华晨不是惟一需要面对这样挑战的自主品牌。如此,当自主品牌基本在同一水平线的时候,他还有时间在研发上再加把力,再拼一把,华晨集团在研发方面也从不吝于大手笔的投入。
“今明两年的投入,肯定要比以前更大。因为明年新的车上得多了。还有,每新开发一个车,后续你都要去一个小变型啊,改款啊,肯定支出就大了。”
对于华晨今年的主力车型,邢如飞坦称主要还是靠去年做的几款成熟产品。但今年必须要做的大的车型有两个,一是乘用车领域的骏捷的改款,这也是骏捷最后一次大的改款;二是商用车领域的大海狮,比现在的海狮要加宽、加长。“我们想把商用车这块撑起来,想冲击一下依维柯和全顺的市场。”当然,要9月份才能开发完成的这款大海狮,对今年整个车产量的影响会很有限。
对于邢如飞而言,他梦想中的“下一台”,是下一个FRV。说这话的时候,他加重了语气:“下一个FRV的尺寸我都想好了,大致会是什么样子的。”而对于记者紧随而至的“能透露一下吗”,他又恍然大悟地说:“这,这还早点儿呢。这车至少得4年之后才能看见。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