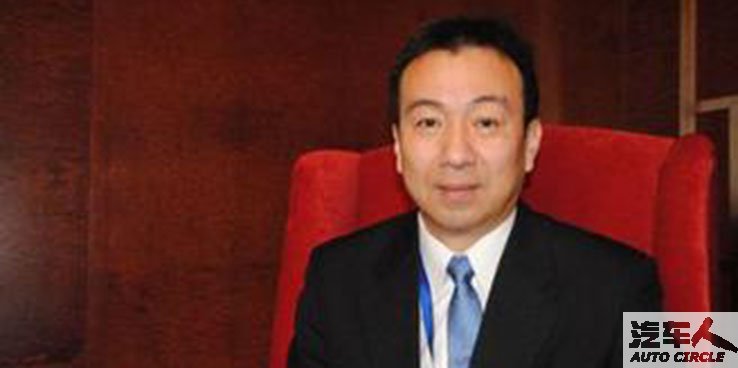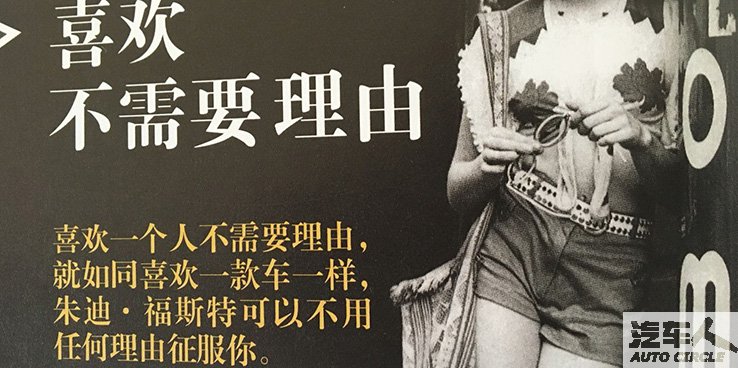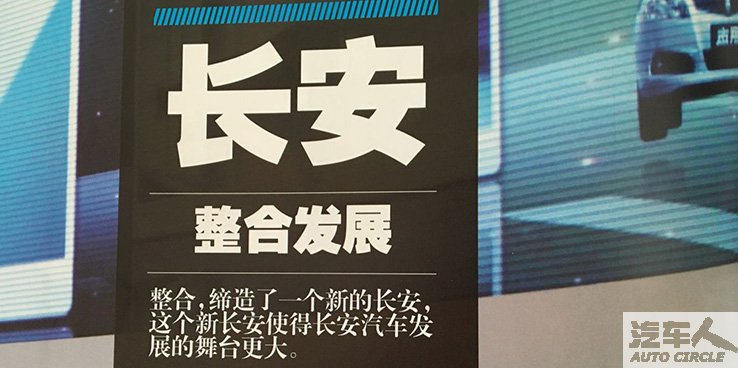春节前,有人告诉我,蒋涛又摔了一跤,住院了。这不止第一次。心想,这怎么吃得消,老人就怕折腾,尤其是经不住摔跤。
春节后我去看他。见我来很高兴。精神也很好,端坐在椅子上。早春三月,下午西沉的阳光透过窗户给病房带来暖意,温润而祥和。
他招呼护工给我拿瓶装水,唤我坐在他的跟前。“在家又摔了一跤,当时没感觉,第二天起不来了,到医院检查说是脊椎骨折,引发旧伤,非动手术不可,这次是全麻……”
在我的印象里,他已是因骨折第三次住院了。
吸取前几次骨折的教训,行动很小心的蒋老还是一不留意歪倒了,跌在铺有地毯的地板上。
“人老了,不服不行。”蒋老无奈地说,这是自然规律,今年我90岁啦!
脸上看不出刚动过手术的样子,气色很好,谈锋甚健。见到我,就像邻里的长者对待晚辈那样,随意而慈祥。
蒋涛是个有威望的人。看他的人多,病了看他的人就更多。晚年对于他并不寂寞,经历和经验以及见地都转变成了人生的财富,包括人们对他的尊重和尊敬。正如马丁·路德所说,这是品格的力量。
说来有缘,我与蒋老交往,素未平生,源于对汽车上的共识。屈指算来,也有十余年了。在外人看来,他是大领导,虽说已不在位,但影响力依旧在,尤其是他给有关方的建议很少落空,重大决策之前事先也会有人来征询他的意见。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尽管年事已高,思维依旧活跃,想问题深刻,就像打开的电脑,反应机敏,全面而不乏建树,对汽车一往情深,无不为之敬佩。但他低调、和善、谦恭,话语素朴、简短,像似开锁的一把钥匙,又像直抵人心的箴言。与他交流不觉乏味,归于平淡的对话,不时闪烁着人生的哲理或感悟。
一
在人们的记忆里,蒋涛是创建国内第一家轿车合资企业的主要领导和参与者之一。德国大众对他很尊敬,称他是“桑塔纳之父”。上海大众首任外方经理马丁·波斯特在他的《上海1000天》中写道,“蒋涛是上海大众项目的‘祖师爷’”。
我想,这些都不是恭维话。历史摆在那里。尤其是汽车业在中国高速发展和繁荣的今天,人们对汽车的关注度开始高起来了,刮起了“寻根热”。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浮现了出来。如在经历了上海大众成立20周年、中国汽车工业50年、改革开放30年等一些列纪念和庆典活动之后,人们把蒋涛这些老人从历史中请出来,饮水思源,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他们的价值在哪里?他们对于今天的业界有怎样的启示?
在诸多报刊文章的介绍中,主要还是侧重于追寻事件发生的过程,来不及对背后细节的挖掘和思考。浮皮潦草、浅尝即止在所难免。
在我看来,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当时却是破冰之举,“是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冒着很大的风险,要顶很大的压力,他们的无畏和勇敢以及表现出来的智慧,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完全是凭着个人的品格和信仰与忠诚找到了一条出路。用今天的话来说,开创了中国轿车与国外合作的历史。而当时,则是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任务,就像使命,光荣而神圣。他们没有私利,无欲则刚。显示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代汽车人的人格魅力。
这是我深入采访蒋涛这些老人在上海大众项目谈判时所产生的印象。蒋涛说,当获知北京以“贸易补偿”的方式上引进一条轿车组装生产线放在上海时,上海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从上至下看作是件大事,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机遇。在蒋涛看来,上海的汽车业和这个行业的改造都曾是他管辖之内的事,包括它的发展和规划,都曾经是他的“心病”。现在好了,国家给项目了,就等于有了方向和希望。作为主政上海机电局的局长,他的想法与市里的想法一致,这不是简单的引进装配流水线的项目,而是关系到一个行业的改造和前途。
凡事从大局出发的蒋涛习惯于从宏观上看问题,有极强的全局观。这是为官几十年的素养。他说,凭他在机电行业的工作经验,借助引进轿车组装线将会为上海工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带来契机。
蒋涛是工业家。上海机电行业有今天雄厚的家底与他在任时打下的基础有关,如上海的气象卫星、远洋测量考察船、民用飞机、核电站等大项目,都留有他的足迹。蒋涛说过,只要北京交办的事,上海没有干不成的。在北京,凡是其他地方干不成的事交给上海就放心了。这几乎成了一种共识。正如饶斌所说,上海是国内工业基础和城市综合能力最强的城市。
蒋涛说,他是首批由地方转入工业的“南下干部”。29岁就当上了上海机电一局的副局长。上个世纪50年代,还专门为《解放日报》写过不少工业建设的社论,60年代还出版过一本《地方工业的改组与改造》的专著。所以,蒋涛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的工作思路都是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经验上。遵循规律,方向对头,务实求真,力求有效。所以,他认为,尽管北京把轿车组装线放在了上海,但不等于这件事就能办成,问题是按80%的出口返销要求与外商合作难以行得通。后来与外商接触证明不行,成功几率甚微。结论是,只有通过与外方合资经营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我们的想法都是来自于从实际出发,也是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
蒋老回忆说,我们把此想法向市里、北京、向中央高层反映。最终,此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的同意。终于打通了发展中国轿车的探索之路。在蒋涛的提议下,这才有了与德国大众合作的故事。所以,上海把一个单纯的出口创汇,轿车组装线的项目改变为与外商合资的项目。这一小步,实乃是历史的一大步。
二
个人的品格有时是最好的名片。请蒋涛组织班子与外商谈轿车合资项目,这是上海市政府的决定。蒋涛说,其间他有3次工作变动(先是计委、后是人大,再是上汽),但是政府的委任一直紧随其后,始终没有松手。原因是对他的信任。
蒋涛一直认为,上海大众谈判项目虽然是地方项目,但实际上它是国家项目。决策和方向都是由中央定,直接受命于北京,上海只是具体执行。它的难度就是在没有一部合资法的情况下谈合资。摸着石子过河。一切都无先例,要靠自己摸索。这种难度可想而知。
在谈判最紧要关头,蒋涛总是从全局考虑,争取主动,推进谈判进程,既要坚持原则,又不能刻板,而是灵活机智,展示了他的经验和领导艺术。如主动帮助外商解决后顾之忧,请中国银行参股,以消除外方对外汇支持的担忧;请中汽公司入股,打消外方怕中汽公司日后有变化的疑虑等。今天看来,这些临时决定的大动作都是在蒋涛几句话的事就搞定的历史,今后恐怕不会再有了。外方为之惊叹不已,这样的个人魅力要比信用证和红头文件还管用,其协调能力难以想像。德国大众曾经试探过,要求中方在3天之内把100辆桑坦纳组装散件的外汇汇到狼堡的账户上。蒋涛一言九鼎,在上海计委的支持下,不用3天就到账了。德国大众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在与一个企业谈合资,而是与一个城市和国家在谈。这就是大众的幸运,不仅没有风险,而且获的了想像不到的丰厚回报。参与当时谈判的德方翻译李文波说,后来他享有直接能与中国的部长和分管的副总理直接通话的待遇,就是来自于高层对于这些老同志们的信任。
也许,德国大众从蒋涛身上看到了他们在中国的未来,正如哈恩一直把饶斌当做自己最好的朋友一样,认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比写在纸上更为牢靠的协议和承诺。后来,他仅凭一份传真(获知一汽与克莱斯勒谈合作),果敢决策,北上找到了耿昭杰,再次获得大众与一汽合资的成功,淘汰了克莱斯勒,书写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传奇。原因是什么?找对了人。
在老外的眼里,蒋涛是有战略远见和决策能力的领导人。在他主政机电一局二十几年中,管辖过500多家企业,人数达30多万人,创造过全国机械行业的七分之一的产值。他亲自抓过上海牌轿车技术“攻关”和“会战”,主持过上海轿车厂的迁址和改造。所以,他对于上海汽车行业的现状心里很清楚。对于拿下上海大众项目他充满了自信。这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过不去的坎。后来我问过他,在谈判陷入僵局,内外交困时,是否想到过会谈不成?
“没有!”蒋涛用坚定的目光说,从上到下都不曾动摇信心,即便是德方派人说不谈时(大众碰到财务危机,想中断与上海的合作项目),还是我们(谈判班子)说服了他们,挽留项目,达成共识,将大项目(15万辆合资项目)改写成小项目(2万辆产量3万辆能力),甚至我们在国民经济计划调整中也碰到困难时,但都不曾放弃与德方谈合资的计划。
这种来自北京与上海的高度默切,显示了老一代汽车领导人的自信和眼光。他们的经验、智慧、决策,对大势的判断和把握,已超出了一个项目的范畴,考虑的都是国家利益。
有人说,蒋涛是上海大众谈判的主心骨和灵魂人物。凡接触过他的人,都认为这是位敢于担当,又懂战略和策略的人,遇事冷静,思考周全,令手下办事的心中有底。
蒋涛是个知识分子味道很浓的人。知书达礼,文质彬彬。其实,他跟我说,他的学历并不高,顶多算是个师范生,17岁参加工作(革命)、20岁当区长、24岁当县长、29岁当局长。这一路走来,几乎都是“自学成才”。我看到过他写的一篇关于上海大众成立20周年的纪念文章,被国内多家权威报刊转载。
提到此事,蒋老说,不是文章写得好,而是讲了真话,是上海大众的发展模式对中国汽车业的发展起到了作用。我拜读过这篇文章,不长,但说得很透,肯定了利用合资企业的经验和技术对发展中国汽车工业的促进作用。现在有不少人对“市场换技术”提出质疑。老先生的文章客观地评价了合资企业的积极贡献。他说,如果回到历史,当时中国汽车业的落后状况现在的人是很难想像。通过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以及合资经营的方式,客观上对加快中国汽车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
“最好的合作是把合同文本锁进柜子里永远不去翻它。”
德国人说,上海大众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都归功于当初谈判谈得好。于是,人们就不得不想到主持这场中方谈判的蒋涛,一位运筹帷幄的智者。
三
2008年年底,蒋涛把我叫到他家去,起草一份发言稿。我知道,老先生在这方面从不麻烦人,这次为什么找我?
原来他在家又摔了一跤,刚出院。市里要举行一次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活动,请了航天、钢铁、汽车、浦东新区4个不同行业和方面参与上海早期改革开放的老干部做大会发言,其中就有蒋老。蒋涛说,市里要得急,我手脚不利索,怕耽误事,请你来帮我起草,最后我来定。他说,你对业界比较了解,我们交流的比较多,你知道我所要表达的想法。随后他拟定了主题、基本思路,大致框架,又准备了几份材料。我说,这不是已经成稿了吗?他说,我眼睛不行,写起来很吃力。
3天后我把稿子捎去,反馈信息是托人带来的一张小纸条,写了几句表示感谢的话。我知道,他轻易不会劳驾别人,现在作为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出的调查报告和咨询建议等也都是亲自撰写。我想,蒋涛真的老了,力不从心。去年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今年体质比去年差了,走路吃力,动作迟缓,年事已高,也符合自然规律,我很安心自足,请放心。”不过,蒋老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思考,比过去更加关注汽车及这个行业的走势。事后有人告诉我,老先生是指定要你去帮他起草发言稿。我想,这也是有原因的。
空闲时,老先生就喜欢与我聊有关汽车的事,或对一些问题发表看法。我是做媒体的,信息比较多,他愿意与我交流。有一次我们谈到未来汽车竞争趋势时,涉及到了一个话题,即企业未来的竞争回避不了文化的竞争。我说,软实力建设将会凸现企业竞争的重要位置,这就需要文化来支撑。而由此提炼精神价值,赋予企业理念等就显得格外迫切。他很赞成,觉得有道理。我补充说,未来的汽车企业要从单纯的制造型的业态方式转变为以文化输出为特征的服务型的业态方式。他问我,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我建议最好先把企业成长(发展)的经验总结出来,或者把历史整理出来,有一个脉络和轨迹,提取共识进行研究,而后向企业价值观和基本理念靠拢。
蒋老说,能否出个提纲之类的东西?于是我拿出了一个总结上海汽车工业30年发展经验的研究提纲。不久,他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和修改之后交给了有关领导,并附了一封信,写道,“近一个月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能否藉国家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把上汽车工业的兴起作一次比较系统的回顾论述,能够成文成册最好;达不到这个要求,就作系统的原始资料作以后参考也好。”
后来上面采纳了老先生的意见,请来一位作家写了一本纪实类的书。
研究企业,把企业的经验和文化固化成精神和理念层面的东西业已成为当今企业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我知道,老先生一直在思考企业在做大之后如何突破新的瓶颈问题。未来的企业责任,不仅要创造和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还要使全体员工认同并被社会认可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
2008年年底,我出差返沪,在飞机上看到《解放日报》头版登载了上海老干部局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报告会的报道,上海的四套班子都出席了,其中就有蒋老的发言。
在上海,汽车业的变化和振兴很能代表这个城市变化发展的一个侧影。如今,“上海汽车”光环四射,领风气之先,备受瞩目。然而,知道其背后艰辛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四
往事如烟。
“凡事开头难”。当回眸一些汽车往事时,蒋涛说,也正因为此,才会把机遇转变为幸运。上海汽车工业由此起步,成了引进轿车合资经营吃螃蟹的第一个案例。
去年,李岚清写了一本《突围》的书。讲的是国门初开的岁月。书中提到了汽车对外开放的事,而且放在了很重要的章节里。证实了当时蒋涛他们提出“合资经营”想法的由来。后来蒋涛收到了李岚清送的这本书,他说,这里记录的都是历史的真实。
李岚清作为亲历者,把邓小平批示汽车可以搞合资的过程完整地呈现了出来,印证了上海破冰之举的艰难。
这是难得的历史文献。多年来,媒体在引用邓小平同意轿车可以搞合资的批示源自于一份珍贵的电话记录,现在从李岚清的书稿里首次看到邓小平批示的真迹——“合资经营可以办”。这就是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已经在考虑对外开放的战略及具体实施的方法和步骤。
今年3月当我再次在华东医院看望蒋老时,他说:“人的一生能干成一二件大事就不错了。”
在我看来,蒋老是一直在干大事、思考大问题的人。离休之后,他对于上汽走出去、跨地区合作,自主研发、要有自己的品牌,对于上南合作的战略意义等,都从历史的高度看问题,视角独特,高屋建瓴,很有针对性和现实性。一位干具体工作的高管曾这样说:“蒋老的意见有预见性。”
据我所知,蒋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研究汽车业的发展上,成了生活的全部,他的不少真知灼见,使在任的主政者备加珍惜。这是老人一生的经验和总结,可谓金玉良言,“是知识累积,生活历练的凝聚,年轻人望尘莫及的智慧与涵养。”
归于平淡的人,说话也质朴,更加睿智。蒋老对我说,想想与我一起出来参加工作(革命)的人,现在几乎都不在了(有的在战争中牺牲了),想想我现在还能工作,深感幸运,赶上了好时候,知足了。
年老,对于蒋涛来说,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生命的自信和重视的责任。在我看来,“体验不到年老经验,是人生中的一种贫乏。”而在与蒋老的交流中,会感受到他对这些诠释更为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厚德载物,大音希声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