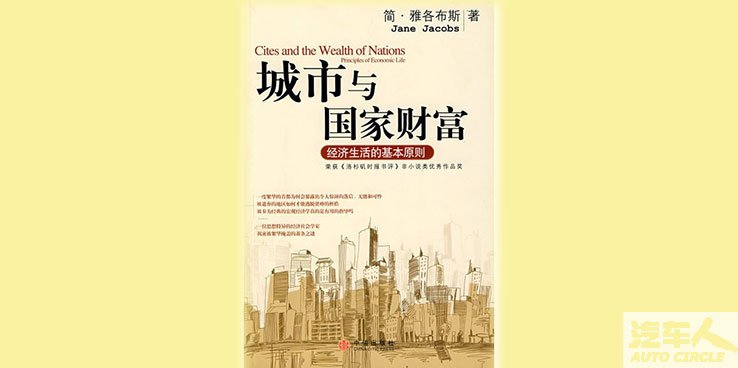
城市对社会学家来说是一个被物质化了的空间,对人类学家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现代部落,对政治学家来说是一个权利角逐的战场,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承载文明的容器,对普通人来说是我们生活的场所,对简·雅各布斯来说,城市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城市与国家财富》可以被看做是作者另一著作——《城市经济学》的姊妹篇,只是前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城市本身发展的研究,而是将视角扩大为城市发展对国家、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加以解读。尽管雅各布斯一生著述甚丰,但人们更愿意记住她的开山之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拘泥于对其城市规划方面的贡献,而忽视了其对城市经济的见解,但《城市与国家财富》作为一部城市经济学著作同样受到了高度评价,美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就认为该书才是雅各布斯的登峰造极之作。
历史上,无论中世纪的帝国还是近代的民族国家都必须面对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一难题。向落后地区提供直接经济援助似乎成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时至今日,由政府和机构提供各种贷款、拨款、补贴和引入大型企业仍被视为改变当地经济面貌的主要手段。但为何受援助地区和国家不仅没有改变现状,反而大多数陷入更为严重的危机,招致当地人民的怨恨,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曾经繁华的城市为何会暴露出令人惊讶的落后和无能?被遗弃的地区如何才能摆脱贫瘠的桎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乃至约翰·凯恩斯的对策都成为雅各布斯批判的对象,这些被奉为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是否真的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具有指导意义?作者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代经济学家的人云亦云不仅造成了本末倒置的政策,而且浪费了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庞大资源。
作为 “城市主义之母”, 雅各布斯从来不回避其对城市重要性的偏爱。她认为经典理论的最大的谬误在于将“国家” 视为理所当然的经济实体,而不以“城市”作为经济分析的对象。进口替代过程在实际上是由具体的城市完成的,而不是靠所谓国家经济,不能区分这二者就会导致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停滞不前。而单纯的信贷和补贴并不能带来发展,无法为落后地区培育出进口替代型的城市。除了暂时性地缓解贫穷以外,贷款和补贴只会造成有惰性的、不均衡的以及永远依赖其他地区的经济模式,无助于创造能够实现自我运转的经济。
但需要指出的是,雅各布斯在强调城市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将城乡二元对立,而是将落后的地区和农村作为城市经济的腹地——乡村必须借助城市进行技术优化和农作物多元化生产,这样就可以避免落后地区成为发达地区的供应基地,掉入与城市进一步隔绝而走向作物劣质化和技艺流失的恶性循环。在此前提下,雅各布斯认为必须从“市场、工作机会、企业移植、技术和资本”这5个互相的方面入手以改变城市内部及其周围的腹地。首先,欠发达地区只有依靠彼此间活跃的贸易往来,形成相对独立的市场才有机会走出困境。因为,如果只是面对发达地区进行贸易,只能加剧对其依赖,最终沦为经济单一的供应基地,仰发达地区之鼻息,还要面对其他落后地区的竞争。一旦出现经济波动,很可能像乌拉圭一样从辉煌走向一蹶不振。这就需要促进一国之内同等发展水平城市之间的互相贸易和进口替代,以此推动经济发展。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经济的扩张就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其次,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和国家的过度依赖大多源于其推动的进口替代政策的失败。区域外引进来的整条生产线或基建被随意安排在偏远地区,一厢情愿地想一次性矫正地区失衡或为贫穷地区提供就业。这些地区往往既没有配套的基础设施,也缺乏相应的人才,这样不仅没有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反而还造成巨大浪费。而真正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只有那些中小企业密集、生产与服务共生互补的城市。如此,从进口替代品开始的自发城市发展才有可能获得可持续的有机有效的竞争力。第三,引进技术同样也要小心,必须与当地和周边经济形成匹配。就像伊朗为了实现现代化,首先引进的是直升飞机制造和组装的技术,对于这个当时仍处在氏族和宗教统治下的国家而言,这无异于让半个国家的工人学习“屠龙术”,不仅成本回收周期长,而且工作机会也不会留给本国过剩的农民,而是被高薪的外国技工所垄断。
回顾全书,可以将雅各布斯的观点总结为——城市的发展和衰落是国家经济兴衰的根本性原因,对那些欠发达经济体来说城市发展更是如此。城市有选择地进行企业和技术引进是前提,依靠自发的应变能力,也就是梅棹忠夫所说的“漂移美学”以实现市场的扩张则是目的。在经济落后地区,一个城市的繁荣所取得的成就毕竟有限,只有这些城市依靠彼此间活跃的贸易往来才能走出困境,并在断裂的发展规律中尽可能延长城市的创造力和多元性。就这样,一位思想特异的经济社会学家,抽丝剥茧,揭密了被繁华掩盖的萧条之谜,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作者/姬康)【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传媒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传媒所有。欢迎转载,请务必说明出处及作者,否则必将追究法律责任。







